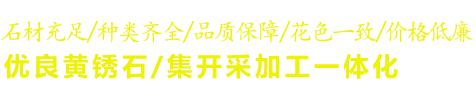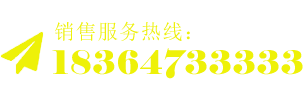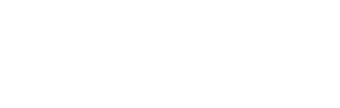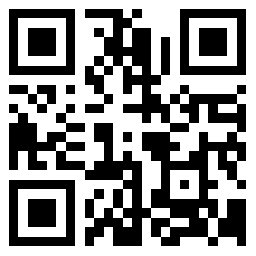西隆山,有“滇南榜首峰”之稱。南部戰區陸軍某邊防連管段內的42號界碑,就在海拔3074米的西隆山主峰。
此地山勢險峻、叢林布满,野獸出沒、蛇虫暴虐,被當地大众稱為“逝世森林”。資料記載,新中國建立以來,僅有幾支科考隊和勘界隊曾登頂過西隆山。
山中本無路,因為有了界碑,便有了路。那一年,邊防部隊組織一支軍地聯合小分隊在無路途、無村庄、無向導的條件下,向這片“逝世森林”進發,蹚出了一條前往42號界碑的路。自此開始,一代代連隊官兵為守護國土而不斷行进。
年復一年行走在西隆山間,腳下的這條路,早已深深印刻在連隊官兵心中。螞蟥谷、絕望坡、斷魂崖……官兵口中的一個個“非正式地名”,無不在訴說著這條路的艱難與危險,但他們的腳步從未中止,他們的信仰從未動搖。
现在,巡邏42號界碑的任務周期已由最開始的6天5夜縮短至3天2夜。前不久,該邊防連一支巡邏分隊再次踏上了前往42號界碑的路,讓我們走近這群邊防官兵,品讀他們在這條路上的故事……
雨霧毛毛的清晨,一聲哨響打破了寂靜。營區的一棵大榕樹下,南部戰區陸軍某邊防連巡邏分隊官兵整齊列隊。清點完裝備物資后,他們駕車駛出營地,沿著盤山公路一路向前。
抵達一片草果林前,能看到一條羊腸小道,邊民稱之為“草果路”,此處就是巡邏分隊步行進山的进口。
3天2夜的巡邏路,吃穿皆靠自己保证,睡袋、手電筒、雨衣、食物……一樣也不能少,每名官兵都會分到一個約30公斤重的背囊。
列兵郭廣林深吸一口氣,跟隨戰友啟程。這是他榜首次執行42號界碑巡邏任務,一想到自己將是同年兵中首位登頂西隆山的人,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境,身上的背囊也不覺得沉了。
這條羊腸小道綿延數千米,扩展至半山腰,再往深處走,便正式踏入咱们稱之為“逝世森林”的范圍。正值旱季,灌木、雜草叢生的地面上都是腐殖土,的岩石上也長滿青苔。一路上泥濘濕滑,官兵們手腳並用還是時不時滑倒,郭廣林也吃了一番苦頭,作訓服很快被染上一片土黃。
“立起衣領,綁好綁腿!”走在最前方的二級上士字鑫提示道。這句話意味著“螞蟥谷”快到了。巡邏分隊在進入一條河溝前停下腳步,開始對身上的衣物縫隙進行“全面封堵”。
河溝中,枝葉上,螞蟥隨處可見。即使防護得非常嚴密,郭廣林還是被“鑽了空子”,一條螞蟥順作品戰靴鑽到他的腳背上。“堅持一下,出了‘螞蟥谷’有一處平地,我們在那裡處理一下。”跟在郭廣林后边的二級上士張祖康安慰道。
到了歇息地,咱们將外衣脫掉,用木棍击打,並相互檢查身上有無殘存的螞蟥。張祖康用鹽水把郭廣林腳背上的螞蟥沖洗掉,將血跡擦干。郭廣林定了定心神,跟隨隊伍繼續向前。
抵達宿營地前,官兵們需跨過2道陡坡。臨出發時,郭廣林自告奮勇背了不少物資,但他高估了自己的體力。爬坡時,郭廣林的腿不爭氣地抽筋了。他本想咬牙堅持,張祖康一把接過他的背包:“靠著旁邊的石頭,緩一緩。”
“加把勁,還有10分鐘就到了……”在張祖康的鼓勵下,郭廣林終於看到2座由木樁和彩鋼瓦搭起的房子。抵達宿營地后,巡邏分隊榜首天的行程進入尾聲。在房子周圍撒上硫磺、草木灰,噴洒驅虫劑,接通水源,撿拾柴火……咱们各司其職開始扎營。
山間晝夜溫差很大,入夜后寒氣加剧,吃過晚餐后,官兵們點起篝火,圍坐一圈取暖。這是咱们一天當中為數不多的輕鬆時刻,郭廣林的神态卻仍然緊張。一路上好幾次險些堅持不住,他擔心自己在明日的任務中給咱们“拖后腿”。
“這就泄氣啦?未來挑戰還多得很,信任本身,一定能抵達界碑。”字鑫拍了拍郭廣林,同他講起9年前的一次巡邏任務。那次途中天氣突變,下起罕見的暴雨,咱们被困在一處山沟。“我們絕不能坐以待斃!”見雨勢漸收,時任連長拄著竹棍榜首個跨上被石塊和淤泥覆蓋的巡邏路,后边的戰友們排成縱隊緩慢行進。就這樣,咱们一步一步脫離了險境。“從那今后,什麼困難我都不害怕了。”字鑫堅定地說。
越是艱難,越要向前。聽了字鑫的話,郭廣林有了更多直面艱險的勇氣,他信任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自己一定能登頂西隆山。
巡邏第2日,天空下起小雨。這一天,官兵們將抵達此行的目的地——42號界碑。
擔心路會越來越泥濘,咱们起了個大早准備盡快出發。“清晨,就聽到一聲聲擂鼓般的悶響,緊隨雷聲而來的,是雨滴撞擊屋頂的聲響。”連隊常指導員起得比其他人要更早些,他覺得西隆山上的雷聲、雨聲並不悅耳,因為在這條險象環生的巡邏路上,雨水是官兵的“敵人”。出發前,他再三提示警醒咱们做好各種准備,走穩腳下的路。
“亞熱帶原始森林中的植物生長速度極快,昨日踩出的路今日或许就沒有了,想要靠人力維護巡邏路幾乎不或许。”后來,官兵們發現山雨在西隆山上沖刷出一道道“水路”,雨天淌水,晴天干枯。在這些河道中,灌木不會生長,還有岩石便利攀爬。
刻記號、刷油漆、系紅布條、記錄獨特的樹根……官兵們開始標記一段段“水路”的方位,再開辟一些路段將這些“水路”串連起來,最終蹚出了今日這條前往42號界碑的登頂之路。
沿著各式各樣的記號,巡邏隊伍冒雨前行。經過半响的行进,郭廣林已有些跟不上咱们的脚步。在一個岔路口,郭廣林發現前方沒了戰友的身影,计划快走幾步抓緊追趕。沒想到死后的張祖康一把拉住了他,並大喊了一聲:“啊!”
好像林間鳥兒啁啾的一呼一應,“啊!”前方也傳來呼叫聲,整支隊伍中止了前進。原來,經過岔路口時,郭廣林辨錯方向,幸亏走在隊尾的張祖康及時發現,通過大聲呼叫找到了隊伍的方位。
這是常指導員為咱们定下的規矩,通過聲音傳遞方位,確保每一位戰友安全不掉隊:“森林裡的情況變幻莫測,不只是新兵,身經百戰的老兵也會迷路。一旦迷路,结果不胜設想。”
此前,巡邏隊伍榜首天行至宿營地不遠處時,伙食員和一位老兵會加快行軍,提早抵達為其他戰友准備餐食。一次巡邏任務中,當大部隊抵達宿營地時,卻不見伙食員和老兵的身影,咱们在周邊呼叫,始終沒有得到回應。
常指導員当即帶著幾名戰士沿著原路回来,在每個岔路口搜尋二人的痕跡,直到暮色彻底籠罩“逝世森林”,迷失方向的他們才被找到。自那今后,常指導員便想出了這個辦法,用呼叫聲讓“咱们始終在一起”。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常指導員和戰友們在巡邏路上點滴積累的經驗還有許多。例如,他們將竹棍一頭劈砍成若干條竹片,有節奏地敲打路邊的雜草和灌木,發出的“嘩啦啦”聲響能够嚇跑蛇虫和野獸﹔盡量逃避黃泡樹,皮膚被它的刺劃傷后不易康复﹔由於當天撿拾的柴火太過潮濕無法點燃,每次抵達宿營地,要儲備柴火留下風干,以備下次运用……有關這條路的記憶,已然刻進每個官兵生命的年輪。
登上最终一座山頭,42號界碑就在前方。常指導員又一次站在界碑旁向遠處瞭望,山河入目,国土穩固。巡邏4個年頭,他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站在這裡:“壯闊的风光中隱藏著大自然的無情,隻有在考驗中磨礪毅力、錘煉本領,才干守好每一寸國土,才干無愧於‘邊防軍人’這個姓名。”
天公也作美,淅淅瀝瀝的小雨終於停了。迎著一路陽光,字鑫依舊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在這條巡邏路上走了近12年,他已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兵。
下午3時,巡邏隊伍回到營區。拾掇完畢,字鑫再次來到榮譽室。每次巡邏西隆山歸來,他都要在玻璃展櫃前,看看那塊已經“退役”的42號界碑。說是“碑”,那其實是一塊老舊的木板,板身上有2道手指粗細的裂縫,上面的字跡已經斑駁褪色。
在連隊官兵心中,42號界碑是一個特别的存在,也是咱们仰视的高地。在該連巡守的8座界碑中,其他7座界碑的巡邏任務都實行建制班輪換准则,唯有42號界碑採取篩選准则,優中選優的官兵才干參加巡邏。
字鑫還記得榜首次申請參加西隆山巡邏任務沒能通過篩選,他一連懊惱了好幾天,開始比以往更努力地訓練。“西隆山巡邏的‘開路先鋒’要背4把砍刀呢。”去別的點位巡邏時,字鑫會把啞鈴片放進背包,鍛煉自己的負重才能,“我不但要參加西隆山巡邏任務,還要爭當‘開路先鋒’!”
在西隆山山脊線上,有一段長達千米的路,途中鳞次栉比的苦竹,像一張巨大的網攔住了官兵的登頂之路,這就是官兵們口中的“竹林陣”。
“過去,官兵需求四肢著地、爬行穿過‘竹林陣’,即使膝蓋和手肘都腫了,戰友們從沒有過怨言,因為穿過竹林,就離界碑更近了。”字鑫說,“巡邏頻率添加后,咱们下決心沖破‘竹林陣’這個阻礙。”
大半年的時間裡,字鑫和戰友們背著砍刀,每次巡邏砍掉一部分竹子,終於開出一條通路。現在這段路已經渐渐有形狀了,不像曾经那般“纏人”。開路官兵仍會在上山時帶上砍刀,砍掉路上極速生長出的竹子。這次巡邏歸來,字鑫帶的砍刀,1把折斷,其他3把鋒刃也弯曲得厲害。
逢山開路,步履不断。連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以無懼艱險為樂,以登頂西隆山為志,以巡邏界碑為榮!”官兵們一次次攀爬高峰,一次次極目遠眺。那攀爬的姿勢,是戰斗,也是執著的堅守﹔那遠眺的目光,有祝愿,也有溫暖的夢。(曹繼可、戚辰飛)

公民日報社概況關於公民網報社招聘招聘英才廣告服務协作加盟版權服務數據服務網站聲明網站律師信息保護聯系我們
人 民 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 2015-20年中國液體石蠟業市場远景及投資咨詢報告2024-12-08
- 偏苯三酸酐概念龙头公司(附名单)2024-12-08
- 2016-2021年中國粗石蠟業市場調查與投資远景研讨報告2024-12-08